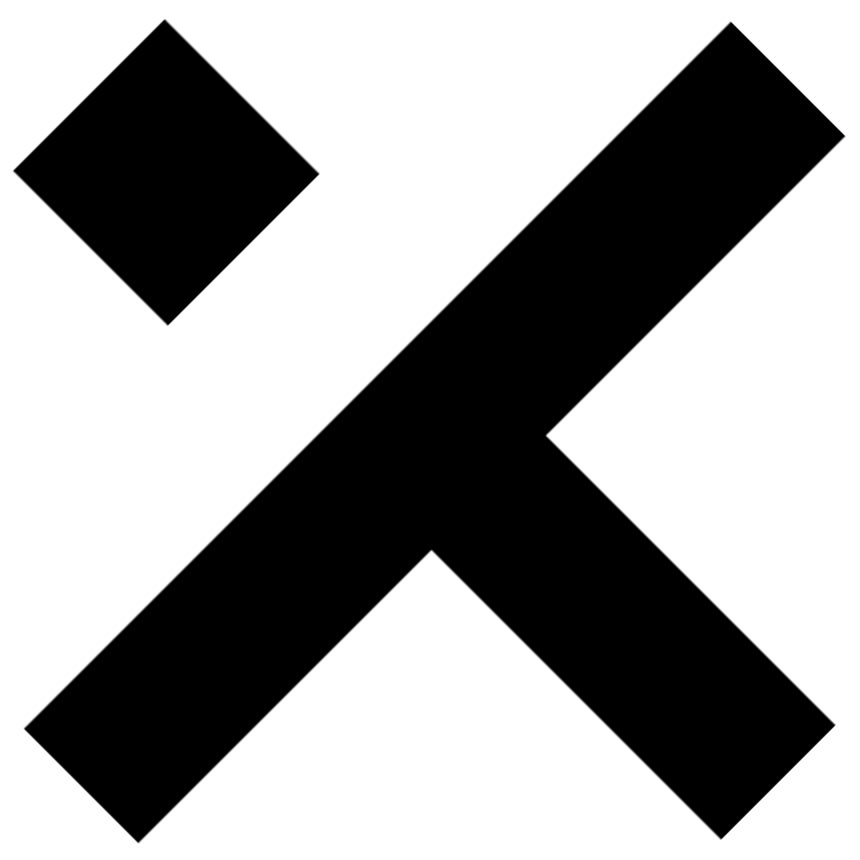“真假”吹哨人
编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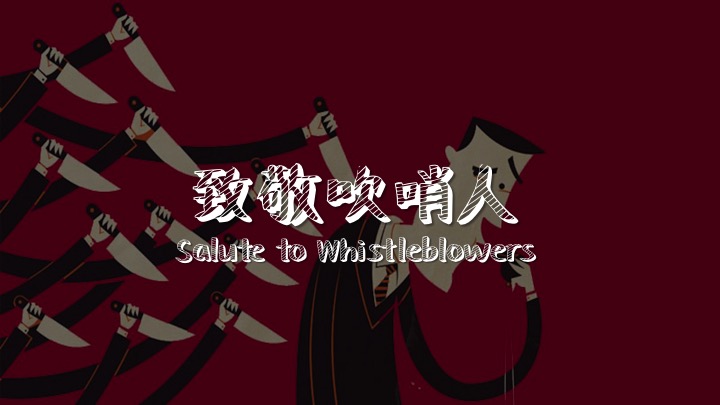
说实话,在大家为李文亮因“被训诫”而鸣不平的时候,我并没有加入这种情绪的浪潮。并不是说我冷漠,而是我对“吹哨人”这个词有更严谨的定义。
李文亮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医生。他感染病毒不幸去世,被追认为烈士,这是我完全认同、也真诚敬佩的。他在面对未知病毒时并没有退缩,继续坚守岗位救人,这是医者的本分,也是他的可贵之处。
但把他说成是“吹哨人”,我始终觉得有些勉强。他在微信群里告诉家人和朋友说“有非典的苗头”,让他们注意防护,并叮嘱“不要外传”。这其实是一种出于亲情的本能反应,并非出于公共利益的主动披露。他没有选择向公众媒体、疾控中心,或者更高层级的卫生主管机构正式举报,也没有试图突破信息封锁。他想保护的,仅仅是他的小圈子。坦白说,这更像是“悄悄通风报信”,而不是“吹哨”。
在我心目中,真正的“吹哨人”,是冒着巨大的风险,为了公众知情权、为了阻止灾难蔓延,向所有人高声疾呼。他们往往背负着组织的怒火、舆论的误解、甚至失去自由和安全。这种行为,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与责任感。李文亮的言行,确实不太符合这一标准。
如果硬要说吹哨,实际上是那个把他截图发出去的人,让整个事件从一个小群体的信息传播变成了公众事件。换句话说,这个“违规”发图的人才是真正让疫情真相浮出水面的触发点。那他是不是更配得上“吹哨人”的称号呢?
说到这里,我不禁想到另一个人——郭伟鹏。如果李文亮能被称为吹哨人,那郭伟鹏,在某种程度上,是否也可以归入这一范畴?
“跑毒”
2020年春天,“跑毒”这个词在中文互联网上一夜爆红。它并不是什么官方术语,而是普通人面对病毒威胁时做出的本能选择。
我算比较“幸运”的一批“跑毒者”,因为我当时人在意大利——欧洲疫情最早暴发的国家。由于国内已经经历过武汉封城,我有了很强的疫情敏感性。那时意大利确诊病例还不过几十例,但我已经几乎不出门了。而意大利当地的人,依旧像往常一样,在阳光下喝咖啡聊天,仿佛一切都无关紧要。
起初我并没有“跑路”的打算。一方面觉得回国得面对十四天的集中隔离、航班上的交叉感染风险;另一方面,我的生活在意大利其实也不算艰难。虽然单身多年,身边没有特别“必须见一面”的亲人,但和父母每周都视频,和朋友们天天在线聊天,也不算孤独。
但一切随着确诊人数的飙升而变了。从破千到破三千,仅仅几天时间。意大利的防疫响应依然迟缓,戴口罩的人几乎为零。我3月3日那天出门去办居留卡续签——一路走下来:打印店、T店、邮局、大街——没有一个人戴口罩。我戴着口罩反倒像异类,受到异样目光的“围观”。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定:必须回国。
其实那时我身边并不缺照顾。我的室友,一个研究生姐姐,厨艺了得,疫情期间几乎包办了我们所有的三餐。我刷碗,她做饭,算是难得的抗疫默契。但再好的人际关系,也敌不过远方父母每日的劝说和忧虑。他们轮番打电话,劝我尽快回国,说“隔离十四天算什么,有家人在,才放心”。
于是,我在3月4日下午买了次日一早的机票,和一位同样身处欧洲、来自广东的朋友一起,踏上了“跑毒”之路。为了降低感染风险,我全程戴着两层口罩,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,只有在转机的空旷角落匆匆喝了一口水。入境之后,在北京机场通过海关时,对话却让我有些意外:
“你是留在北京,还是去别的地方?”
“回河南。”
“买票了吗?”
“买了,下午的高铁。”
“行了,你可以走了。”
就这样,我直接离开了机场,独自乘坐地铁前往北京西站,随后搭乘高铁从北京直达郑州——整条旅途,没有一个人对我这名来自海外、属于高风险类别的旅客进行有效干预或隔离处理。
我是在入境前提前向老家防疫部门做了报备,所以在郑州东站就有人接我去集中隔离。但这个流程完全建立在我的主动配合之上,如果我没有报备,如果我临时更改目的地,如果我哪怕随意走动一小时——后果会如何?
从这个经历可以明显看出,彼时的防疫系统还存在明显漏洞,尤其是在入境后的国内转运、追踪环节。制度信任的是旅客的“自觉”,而不是机制的闭环。而这些空白,也正是郭伟鹏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土壤。
“海关”:制度漏洞的暴露口
那么,为什么说郭伟鹏也可以算作某种“吹哨人”呢?
郭伟鹏,并不是留学生,也不是滞留海外的普通旅客。他是在疫情已经开始全球蔓延的背景下,专程跑去意大利看球赛,还顺手做起代购生意,试图在混乱中牟利。整个行为过程,既非刚需出行,也毫无社会责任感可言,反而是对疫情态势的公然轻视与冒险。作为一名从海外返回中国的人员,他瞒报了行程、未如实申报自己的健康状况,最终在回国后的“自由活动”中确诊新冠。这导致了在当时基本已经控制住的疫情,再次在国内出现传播链,造成了极大的防疫压力。
毫无疑问,他的行为是自私的、不负责任的。他既不是“吹哨人”,也无法被解释为误判或疏忽。他是个典型的高风险输入源,对自己、对他人都构成实际威胁。但也正是这起事件,暴露了当时中国在口岸防疫管理中的一个巨大漏洞:即便是在国外疫情严重、病毒传播性极强的背景下,仍然存在“申报之后自由通行”的可能;没有闭环转运、没有强制隔离,系统完全依赖个体“如实申报”和“自觉执行”。
正因为郭伟鹏事件的“震撼”,防疫体系迅速收紧。自那以后,“点对点接送”与“集中隔离”成为归国人员的标准流程,各地口岸的防疫措施全面升级,行程申报机制也趋向严格。这些制度的出现,有效遏制了后续境外输入病例对本土的影响,保障了国内大多数人的安全。
换句话说,郭伟鹏用“负面教材”的方式,推动了制度的完善。他没有有意识地“吹哨”,但却在事实层面上,“暴露”了防控中的漏洞,并迫使机制加速更新。
那么,从这个角度来看,他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一种“被动型吹哨人”?或者说,有时候推动机制进步的不一定是正面典型,而是一次次足够严重、无法再容忍的失败。
“训诫”:公共秩序的防线
李文亮的“训诫书”,一度成为全民愤怒与悲伤的导火索。在那个信息极度匮乏、公众恐慌蔓延的时间点,他“因言被罚”的遭遇被迅速放大,成为无数人情绪宣泄的出口。大家高喊“我们要言论自由”,希望未来再也不要有人因为说出真相而被打压。在很多人眼里,李文亮是一个“被训诫的英雄”。他的微信群截图流出后,社会情绪迅速升温,很多人将他视为疫情“第一位吹哨人”,甚至是制度缺陷的受害者。
但我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判断。
李文亮在非官方的私人聊天群里,传播了“非典类病毒出现”的消息,并提醒朋友“不要外传”。他并没有通过正式渠道上报疫情,也没有经过专业核实,而是在一个模糊、半公开的圈层中释放高度敏感信息。这类未经证实的“类传言”,在疫情早期阶段极容易引发恐慌和混乱——人们囤粮、囤药、误判风险,社会秩序可能因此受到冲击。
疫情爆发之初,信息传播的准确性与统一性本就是防疫体系中极关键的一环。李文亮的行为虽然可能出于善意,但他绕过了信息发布流程,本质上制造了额外的“认知冲击”。如果人人都以“私下消息”的方式去预警他人,整个社会将面临信息碎片化、真假难辨、决策错乱的局面。这不是真正的“吹哨”,而是风险的扩散。
所以,当时对李文亮的“训诫”,从制度角度来看,并非完全不合理。它代表的是对“非正式信息传播”所可能造成的影响的一种应激控制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舆论中受到同情,就全盘否定制度在防控初期所必须维护的信息秩序。
更值得反思的是,李文亮的言行被社会情绪无限放大,甚至神化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“什么是合理的信息披露、什么是有效的风险沟通”的理性讨论。如果不加区分地将“说了某些话”就等同于“吹哨人”,那么我们反而是在降低社会对“责任披露”的要求门槛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,李文亮的“训诫”就像一次制度性错位的公开暴露:它把“流程正确”和“实情披露”之间的冲突推到了台前,也迫使体制在随后的疫情控制中,开始更多考虑如何在危机之下放开“非官方路径”的信息反馈机制。这种反馈后来体现在专家意见、社交媒体报告、地方疫情通报机制的逐渐多元化。
而另一边的郭伟鹏,虽然没有因“说话”而被训诫,却因“隐瞒”被社会唾弃。他的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制度的漏洞:在当时,没有闭环的归国人员管理流程,也没有足够严密的追踪机制。他的“漏洞”,像一面镜子,把风险暴露给了整个防疫系统。
结语
当“吹哨人”一词被频繁提起时,我们需要更冷静地思考:什么才是真正的警钟?李文亮因私下传播未经证实的高风险信息被训诫,却在舆论中被过度神化;而郭伟鹏因隐瞒行程、传播病毒而受到谴责,却间接推动了归国人员“点对点闭环管理”的完善。一个被感性塑造成英雄,一个被理性修正为教训。
在每一次突如其来的危机中,都是普通人做出无数关键选择,才换来了秩序的延续。而我们,是否真正理解、记住了那些默默守住岗位、坦然报备、认真防护的“无名吹哨者”?
我们真正需要的是:在面对未知风险时,能规范信息传递、及时上报风险、遵守程序并承担责任的公民;同时也需要一个制度,能够及时接收、处理、响应这些信息,而非只惩罚或推诿。
吹哨,不只是勇气的象征,更是责任与规范的体现。
我们不应该用“英雄”或“罪人”的简单标签,去模糊公共事件中应有的分寸与原则。相反,我们更应当警惕:在危机中,最宝贵的并非情绪正义,而是机制升级与社会理性。
- 0
-
分享